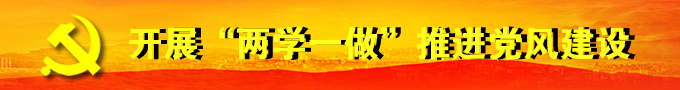9月8日,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李一氓回忆录》一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李金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中联部原部长钱李仁、朱良,文化部原部长王蒙以及等出席了座谈会。会上谈及"文武双全"的李一氓,王蒙提到其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时,亲自曾派周汝昌一行苏联的列宁格勒察古本《石头记》,为《红楼梦》研究做出了贡献。
《李一氓回忆录》是李一氓生前历时八年亲笔写成,讲述了作者亲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书中对南昌起义、上海地下工作、万里长征、皖南事变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了许多生动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也顺带提及了建国后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包括"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
李一氓的"朋友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鲁迅、郭沫若……
"我出生在天府之国--四川彭县。这个县在唐宋时期叫'彭州',不隶于成都,而是与蜀、汉各州等齐名,政区级别是很高的。"这是《李一氓回忆录》第一句。李一氓,这个名字年轻人或许已不熟悉,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诗人和书法家。
而其经历却有相当"辉煌"的一笔,由著名党史专家何方先,在《李一氓回忆录》再版序中提到:"他(李一氓)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为统战去见四川军阀刘湘的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还在长征前夕介绍郭沫若入党;多年还在长征前夕共同介绍郭沫若入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入党;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过―个时期;和邓小平也熟,长征时遵义会议期间还同住―屋,等等。"在书中,李一氓也一笔带过其与林语堂、丁玲的私交。
会上,何方也提到李一氓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不攀领导、不挟名人以自重。"在书中他说:"有―次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有关同迅"左联"等的接触写详细点,他也拒不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
王蒙:李一氓曾解决我的困惑 让列藏本《红楼梦》"回归"意义重大
李一是前中顾委常委,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十年,他在新时期全国的古籍人才培养及整理出版工作,以及他高达两千三百余册的词书收藏,还有他的书法造诣,都使他成为在文化界很有影响的党内领导人。
中华书局党委书记徐俊说:"我曾在李老身边做了一些工作,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文气、博学、通达。"他提到李一氓对古籍出版整理的诸多贡献,包括编辑出版浩瀚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全辽文》、《全元诗》、《全明词》、《全清词》、《台湾府志》等重点项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八十年代李老,派周汝昌等先生赴苏联考察'列藏本'《红楼梦》。"
据说,清道光十二年(公历1832年)由俄国传教士带回手抄本的《石头记》。这个八十回的本子缺五、六两回。这个本子流失海外约一百五十二年。1984年,国家启动了古典图籍整理编印的文化积累工程,李一氓挂帅,他决定派周汝昌、冯其庸、李侃等前去苏联列宁格勒考察那部古本《石头记》,周汝昌先生对这个藏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会上,对《红楼梦》也非常有研究的王蒙,也提到"李一氓组织迎回的列藏本,对红学研究意义重大。"其间,他也提到李一氓对其在文学上的鼓励,"李一氓的小院,曾是我得到清晰指导和鼓励的源泉。"

李一氓/人民出版社/2015-8
自序
我从1925年起参加革命,但在中国革命整个历程中,是很平庸的,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贡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引导我走向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了1925—1927年大革命和南昌起义。
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作为战士中的一员,我幸好还能顶得住,没有在失败面前意志动摇,1928年到1932年,在上海做了五年的地下工作。这五年中,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一点认识。后来在江西苏维埃运动中,经受了农村工作实践的锻炼。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急风暴雨时期。今天想来,如果当时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对自身的锻炼可能更有益处,可惜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而后是长征,这是中国革命武装的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次也没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长征是伟大的,但我只能说是长征幸存下来的一个战士而已。“不到长城非好汉”。此后我就在长城内外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黄土高原上奔驰了两年。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到来,也使红军得到一个最大的战略转机。我就身不由己地来到山明水秀的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工作。可是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给我留下一个终身难忘的遗憾。还好,我又来到了抗日根据地苏北淮海地区,竭尽了我的中年力气,周旋敌后。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一直怀念那个地区对敌斗争的人民,跟我共同度过这场苦难的干部和那么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
经过三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了全中国。全国人民都高呼“我们解放了!”,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自己历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长征当中有一本日记,按天记下了晴雨、行军里程,经过什么省、什么县。曾根据它写过一篇长征记事———《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但是这个日记本子在皖南事变中埋在长满茅草的山上了。后来担任驻缅甸大使,写过一个五年(1958—1962)之久的《驻缅日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掉了。但我的这个回忆录,只记录到1949年为止,即或那本日记没有烧掉,对于我这个回忆录也没有什么帮助。
同时,我又没有做记录的习惯,参加任何会议都不做记录,因为第一怕不准确,第二怕丢掉。因此当我动笔的时候,没有什么亲笔的记录可供作回忆的具体依据。
近几年来,许多同志对于从党的创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个时期的回忆著述很多,也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已经使人目不暇接。但还有许多过去的文献在革命过程中已大量丧失,某些历史争议一时也难以判断。我这个涉及四十多年历史的回忆记录,也仅仅是我自己的回忆记录;无非是我参加大革命、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自己所能记忆的个人经历的记录。
原来自己并不想找这个麻烦,写什么回忆录。首先是时间、地点这两者,我现在记录下来的,就很难说是准确的;有许多稍为涉及一点议论的地方也很难说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有些事情,作为历史来讲,应该由党史学家去解决。我并不是党史学家,我只能表达一种极为疏浅的、简单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专案小组,要我写自传,我奉命写了,共一万多字。“文化大革命”后,这个自传退给我了。但经过党内审阅之后,党组织不知为什么看上了它,据说抄了一个副本留在组织部门了。既然这样,不如把它充实一下,让它更有内容一些,更有历史趣味一些。所以从1983年起,拖拖拉拉,字数虽然增了三十倍,时间却费了八年之久。
在专案组要我写自传的时候,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准“丑表功”;第二,不准“攀领导”;第三,不准“安钉子”。既然是受审查写的自传,这个自传自然就是“供词”。供词是供认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错,当然不是要供你有什么功、你有什么劳。所以他的第一条不准,是有它的道理的。供词是要作为判刑的依据的,假如你供的那些罪、那些错,都跟领导牵连上(不是说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那些倒台了的领导),就把你的罪、你的错减轻了,或者说是淡化了。所以第二条不准,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所谓“安钉子”,大体上就是写文章的一种手法,即“伏笔”。譬如供词中有一句话,粗看起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却可以在将来作为翻案的依据。他要把你的罪和错定死,使你没有改口的余地。所以第三条不准,更是有它的道理了。这三个不准的条件,我在写那个自传式“供词”的时候,大体上是照办了的。因为我想过,我在党内这几十年来确无功劳可说,上依党的方针政策,下靠群众,自己原无什么功劳。“丑表功”也好,“美表功”也好,都无可表之处。至于“攀领导”更说不上,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我并不想挟某一位领导以自重。要是有什么罪、什么错的话,我都愿意自己承担起来。至于“安钉子”,我有“钉子”就安,而且是明明白白地安上去的。没有“钉子”我也没有瞎安,以图侥幸。

李一氓书法
妙得很,我的那个专案组的王组长,看了我的自传以后,居然当我的面,大为表扬,说我这一万多字的“供词”确实没有“丑表功”、没有“攀领导”、没有“安钉子”。对此我的印象很深,感觉到写自传应该承认有这么三条原则。1983年我开始提笔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认定这三条原则还是应该遵循的。虽然它不是供词,谁也不能凭它来定罪,但总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刻都注意到,作为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做了什么工作就写什么工作,犯过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当然在字里行间我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攀哪一位领导。至于所谓“安钉子”,现在更说不上了,有什么“钉子”好安呢?
这样,1983年我就开始动笔了。第一章童年、学生时代,第二章大革命,第三章上海地下工作,第四章瑞金、苏维埃运动,最后第十章过眼云烟,这些篇章都是我自己动手的。写得很慢,直到1985年才写完。后来精力不济,还要搜求材料,就请李克同志协助,我口授,他笔录。大概1986年补完大革命一章,也补完瑞金一章。1987年写了第七章皖南,第八章淮海抗日根据地。1988年补完皖南一章,写了第九章大连。1989年写了第六章陕西、甘肃、宁夏。1990年写了第五章长征,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是早在1936年写的,后来收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样全书就算写完了。
1986年到1989年写得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利用暑假。1986年的暑假是在上海金山化工厂的宾馆度过的,1987年到1989年的三个暑假是在北戴河度过的。其他的时间之所以不能集中,因为在这些年份内,我曾两次出国,每年还要大大小小生点病,住一两个月医院。特别是时间间隔最长的有六十年,最短的也有四十年,回忆起来不容易。有时还得去翻阅些文献、档案资料和个人著作,或写信给同志们问清情况,这样来引起思路,订正事实。最后还得通过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才能形成互相照应的、有机的章节。这就占据了比写作还要多的时间。
因为有些同志在我写的某些章节的特定时间内共同工作过,个别同志正在研究历史上的某一课题,熟悉情况,所以我曾请胡立教、王辅一、李志光同志审阅过有关皖南事变的一章,请杨纯、谢冰岩同志审阅过有关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一章,请韩光同志审阅过有关大连的一章。至于全稿,我请何方和陈易同志审阅过。1989年又请王泽军同志把全稿做过一次文字整理和体例统一。最后为郑重起见,我把整理过的稿子请崔高维同志再以他做编审的学力和经验,从头到尾在文字上,在逻辑上,并尽可能地在历史事实上,最后在行文体裁上,加以审订。我感谢他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当然全书的写作责任要由我个人承担。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索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而已。
一九九〇年立秋,于北戴河
李一氓回忆录

1961 年,任驻缅甸大使的李一氓(左一)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中国工业展览会剪彩仪式。
上海地下工作(节选)
回到上海后,因为生活关系,由郭沫若提议并主持,在创造社由我和欧阳继修(华汉,阳翰笙)去编一份三十二开的小杂志《流沙》,刊名即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后在潮汕失败的那个地方的地名(属广东揭阳)。每月编辑费六十元,我和欧阳平分。
这半月刊,1928年3月15日出第一期,4月1日出第二期,4月15日出第三期,5月1日出第四期,为五一特刊,5月15日出第五期,5月30日出第六期。我用了两个笔名,写诗用L,写杂感《游击》用氓,这是仿《布尔塞维克》上撒翁的《寸铁》,写短文章用一氓或李一氓,几乎都是些马克思主义启蒙文字。其他的供稿者,据现有目录当为:王独清、黄药眠、邱韵铎、龚冰庐、华汉、成仿吾、许幸之、李铁声、朱镜我、顾凤城……。有几个名字,今天已不能记忆为谁了,如谷音、振青、唐仁、N.C.、弱苇、启介、鹿子……。第一期的第一篇为《前言》,署“同人”。这个《前言》今天看来是相当“左”的,但还不是“可怕”的。我们反对中国式的文人,什么浪漫王子的歌者、发梦的预言家、忧时伤世的骚人等,自称为新生活中的战士、斗争中的走卒;我们反对风花雪月的小说、情人的恋歌,自称为粗暴的叫喊;并且侈言春雷没有节奏,狂风没有音阶,我们处在暴风骤雨的时代,因此应该是暴风骤雨的文学;而且确信“只有无产阶级才最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唯有受了科学洗礼的无产阶级才最能有明确的意识”。就当时来说,这个《前言》,作为这本小杂志的指导方针,恐怕太伟大了一点,但还是立得住脚的,意思是正确的。可惜由于当时的环境,国民党的极端反动,这本小杂志只出六期就夭折了。在办这个小刊物的同时,章乃器,当时是上海一位银行职员,亦办了一个小刊物叫《新评论》,其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论,观点实在模糊。如说:“第一是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阶级斗争的痕迹。第二是我们需要阶级斗争么?不过斗争总先要识清谁是压迫阶级和谁是被压迫阶级。像中国的情形,说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或治者阶级对于被治者阶级的压迫,都是不透彻的。因为乡间的劣绅和城市间的帮匪,往往都是无产阶级,他们不但压迫无产阶级,同时也压迫资产阶级,甚至还压迫治者阶级……”因此在《战线》上,弱水作文加以批驳。在《流沙》上,我在一篇叙述马克思学说的短文后,也捎了一句,劝他们“不妨去读几本社会科学入门书”。
《新评论》把这两件事联系一起,写了一封信给《战线》和《流沙》,说我们批评态度不好,避开问题的实质。看来要求他们去懂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他们是当时上海少数资产阶级职业青年知识分子,同国民党没有联系,用不着去同他们对立。我们分开来,由潘汉年代表《战线》,答复他们一信,“流沙同人”代表《流沙》答复他一信,认为他们的来信有诚意,很好,不纠缠这些争论,说这些争论由弱水和李一氓他们分别答复。一封公开信和两封复信,同意由《新评论》刊出(见《新评论》一卷十期,1928年4月)。因此我在《流沙》第六期上,写了一篇《我的答复》。因《新评论》的信上,有“区区社会科学平凡人都能懂得”的话,所以我还是劝他们“不妨去读几本社会科学入门书籍”。至
于弱水是不是有答复文章?弱水又是何人?现在也难于考证了。我们和《新评论》的论争没有继续下去。这个刊物是个小三十二开本,章乃器个人署名的文章,每期都有两三篇。它和1940年到1944年在上海刊行的《新评论》,是两回事,恐怕现在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几本了。《流沙》,一本小杂志,存在不过三个月,上边也没发表过什么长篇大论。
因此,无论在当时和现在,它都没有闪出什么火花,可以影响当世,留给后人。不过它和我个人的生命,却有这么一瞬的牵连,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苦心地去翻阅这个小刊物,想断章取义地从中找出一些攻击我的文字罪过。现在我重温少作,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有幼稚的地方,但自认为这正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气概。要自我欣赏的话,那些《游击》栏的杂文,那些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短文,倒无所谓,而《太阳似的五月》、《春之奠》那几首诗,还是有真情实感的。大革命失败了,自己怎么想的,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都多多少少反映在这份小刊物上。这三个月没有白活。《流沙》是1928年6月停刊的,几经酝酿,又从1928年11月起,仍用创造社的名义,出版《日出旬刊》。这也是一个短命的刊物,只出了五期,到1928年12月15日就停刊了。这个刊物是一张报纸的十六开大小,全部横排。内容偏重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很少涉及文艺,没有发表过一首诗。写稿的人有沈起予、华汉、李初梨、李一氓、龚冰庐,其他有些署名已很难对上号,只有
沈绮雨当即沈起予。我又另用“孔德”的笔名,写过几篇短文,因为要用孔老二后代的名义和林语堂开个玩笑,所以用了这个带孔姓的笔名。在《新思潮》第二、三合期上,也用这个笔名,写过两篇书评。《流沙》和《日出旬刊》之间有四个月的空白,这个旬刊是否仍由欧阳与我合编,是否仍向创造社拿编辑费,已不能记忆。旬刊仅出了不到两个月,这些问题的是或否,也就没有弄个一清二楚的必要了。
1930年4月至5月,我又负责编了一个小刊物《巴尔底山》。五十年之后,1980年4月,我写过一短篇回忆录《记巴尔底山》(见《一氓题跋》)。我在这小刊物上也写了些短文,其笔路和在《流沙》上的《游击》差不多,刊物取名也类似。因此也就不再另行重述了。因为是巴尔底山(即Partisan,游击队之谐音),所以把撰稿人冠以“队员”之名,有一个三十个队员的名单,附在第一期末。即“现在就将基本的队员,公布如后:德谟、N.C.、致平、鲁迅、黄棘、雪峰、志华、熔炉、汉年、端先、乃超、学濂、白莽、鬼邻、嘉生、芮生、华汉、镜我、灵菲、蓬子、侍桁、柔石、王泉、子民、H.C.、连柱、洛扬、伯年、黎平、东周”。我的笔名,没有用先前用过的L、一氓,而是另用了“德谟”,即为我原名民治英译汉,德谟克拉西之前两字。还用了“鬼邻”,因为我那时住在静安寺路东头赫德路(今常德路)的某里某号,紧靠万国公墓(今静安公园),与洋鬼子为邻。但此一笔名后来并未在他处用过。


 | 书画频道
| 书画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