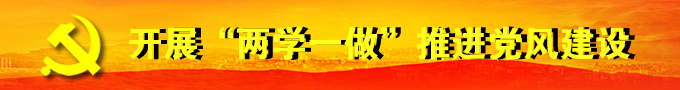前些天买回了一本故宫藏照,整理书架时,便抽出了很不少关于晚清的笔记,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起来。这一翻不要紧,竟忽然对慈禧照相一事,有了探究的兴趣,并牵三挂四地联想不止。也罢,今天爽性将其记录下来。
在北京故宫现存档案里,有慈禧的大量相片,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在颐和园所拍的“标准照”。尤其是一张《宫中档簿?圣容帐》记载为“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容”的照片,现存一百零三张,每幅高七十五公分、宽六十公分,衬裱在硬纸板上,镶在雕花金漆大镜框中,并分别放在紫檀木盒内,外裹明黄色丝绣锦袱;估计这些照片并非留作自我欣赏,也非意在留藏宫中,是准备用于外交礼仪,作为尊贵赠品的。当初晒印时,不会取一百零三之数,可见已送出了若干,但所送出的,又不是太多。查记载,一九〇四年德国皇储来华,慈禧接见,曾取出一幅,托其转与德国皇后,“用黄亭抬至外部……加车随德储君赴津,送至柏林,藉代游历”;还送给过什么“外宾”至目前尚无人细做统计。
这张“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容”的照片,我们可从紫禁城出版社编印的《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里看到,与这张拍摄在差不多同时的,还有很多张“圣容”,格局大体相同,但布景、服装、饰物与慈禧所摆姿势各有变化。从布景上看,宝座与扇基本不变,宝座后的屏风,则有孔雀、寿松、丛菊等多种变化,宝座两侧的摆设也往往各不相同,或瓶荷安泰,或百果献寿……地面所铺的地毯也时有改换,但变化最大的则是慈禧本人,仅所换的服装而言,便有团寿字、竹叶青、缠枝莲、蝶花、寿蝶等多种纹饰;而她的装饰品,就更是不断地增添组合,有戴护指照、佛珠照、东珠照……有几种是戴明珠披肩拍的,那披肩系用三千五百粒大如黄雀之卵、俱精圆纯净的天然珍珠连缀而成;更有趣的是慈禧从端坐的姿态,渐渐演变为各种比较随便的坐姿,以致最后干脆站起来拍,甚至于拍出了一手簪花、一手揽镜自照的“表演照”。
一九〇三年慈禧六十八周岁,她的七十华诞的庆典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大量地拍照,据说也是有关的节目之一,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她的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拍的,那位宫廷摄影师便是勋龄。勋龄是一度担任清廷驻法、德等国大使的贵族裕庚的儿子,他和另外一弟二妹从小随父母到西欧生活,在法国入陆军学校学习,在那里学会了摄影,并具备相当的水平;一九〇三年裕庚全家从欧洲返国,勋龄和弟妹都被召进宫中,因为当时慈禧大量时间是待在颐和园里,所以他们也就大量时间在颐和园里为慈禧服务,勋龄管理颐和园的全部电灯,他弟弟则管外国运来的小火轮,因为他们是男的,所以能挨近慈禧的时候不多,而且每晚必须出园回家去睡;可是他的两个妹妹就幸运多了,大妹妹德龄和二妹妹容龄(也有写作德菱、容菱的,因系满语译音)都成了慈禧所宠爱的御前侍从官,因为她们都通英语和法语,所以实际上主要充任慈禧接见洋人时的翻译,慈禧对外洋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两姐妹来完成的。慈禧封德龄为公主,并欲把她指嫁给权倾一时的荣禄的儿子,可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德龄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一“恩典”,她借到上海探视父亲之机,再没返回宫廷,并终于自主地嫁了一个美国人,后并用英文写成颇有影响的回忆录,前一部分是关于童年的回忆,后一部分则是关于在慈禧身边担任御前女官的回忆,她的回忆录,特别是后一部分,颇具价值,很早便有文言与白话两种译本,那里面,对她哥哥勋龄给慈禧拍照,以及美国女画家卡尔给慈禧画像,都有很生动详尽的记述。
据德龄记述,一九〇三年在颐和园中的拍照,是慈禧初次照相。此说尚可讨论。因为徐珂的《清稗类钞》里,有关于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应诏为慈禧在颐和园中拍“簪花小照”的记载,并称照完后当天便于庆王邸消夏园中冲洗,慈禧不仅“许以千金之赏”,并“内廷传谕又支二万金”,一张照片获如此厚酬,惜乎当年尚无《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否则定当入选。日本人为慈禧拍照事,当在庚子(一九〇〇)年前,那时宫中一定已有拍照之举,因为在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旧照片里,虽无慈禧和光绪的,却有一张珍妃的,珍妃于八国联军逼近京畿,慈禧挟光绪“西狩”,临行前被推于井中了,所以她的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宫中即有照相事的不争之证。但不管怎么说,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勋龄为慈禧的拍照,才使慈禧终于迷恋上了西方这一“奇技淫巧”。
照相术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一般史家都认为成型的照相术,是由法国人路易?达盖尔与英国人塔尔博特在互不相通的情况下,分别发明出来的,前者的成像方法就被称为“达盖尔法”(Daguerreotype),后者的则被称为“卡罗法”(Colotype),时间约在一八三九年,很快风靡欧美,并传进中国,一八四四年八月,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到澳门同法国史臣拉厄尼谈判签约,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国官员向他索取照片,他毫不为难,立即拿出一式四份分赠,并将此事奏予朝廷:“(洋人)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小照”便是当年中国人对照片的称呼。笔者一九八八年在法京巴黎的摄影博物馆中,见到过耆英的“小照”,署名朱利?埃及尔(JulesLtier)摄,此摄影者系当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到一八六〇年左右,在上海、广州出现了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并出现了一些中国最早的摄影家;北方虽此风晚到,但到一八七五年时,天津也出现了若干家照相馆,其中最著名的有梁时泰照相馆、恒昌照相馆等;至于京城,直到一八九二年才有泰丰照相馆开张,虽后来,却居上,这家照相馆拍摄了大量京剧剧照,并在中国最早拍摄了“活动照相”(即电影)。就这样,照相术这个“泰西怪物”,从洋而中,由南而北,从官场到民间,一步步向宫廷围渗,并终于在一九〇三年,获得中国当时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青睐。
慈禧个人的奋斗史,恰重叠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她个人而言,那真是极大的成功--竟打破了清朝列祖列宗的几层禁忌,在同治、光绪两朝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在临死前还亲定了小皇帝宣统;在半个世纪里,她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她那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挑战的政敌,又始终过着随心所欲的相当富有审美情趣的帝王生活,正是在她的亲自培植下,一个至今仍令全世界惊叹不止的艺术瑰宝--“北京歌剧”即京剧,正式形成;但在当代史家笔下,慈禧却是一个几无争议的反动人物,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她的确都扮演着可耻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屠夫角色,她的穷奢极欲、武断乖戾、反复无常,更令人厌恶唾弃。中国近代史的那五十年里,也许无论谁占据那最高的决策地位,也无法逃逸于整个中国的悲剧性命运,因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某些深处的机制是难以抗拒的,但慈禧个人的擅权、保守、狭隘、顽固,有时甚至表现为一时震怒、一刹错念,而以她个人的那点绝对无法适应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见识和无人可以驭制的乖戾性格,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具体进程,并波及几乎每一个那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也为她死亡以后的中国埋伏下了无数的玄机。
据德龄回忆录的第二部《清宫禁二年记》,慈禧在颐和园中,心情好时,“极形仁慈”“如慈母焉”,她在德龄的住房中看见了德龄在法国拍的相片,惊而言曰:“噫!此皆尔之影片乎?较之画像佳甚,且益逼真,曷为不早示余?”(为简省字数,引用德龄回忆悉取文言译文,下同)后得知管电灯的勋龄即擅摄影后,立即召见,并迫不及待地就要他给自己拍照,命曰:“余拟先摄一乘舆视朝之状,然后再摄他影数种。”第二天天气晴好,勋龄携摄影器数具,候于宫院内,慈禧步入院,--视之,听勋龄详解摄影之法后,即命太监一人立于器前,她则由聚光镜片中,望其形状,旋忽惊问曰:“尔首曷为颠倒?!”听了德龄一旁的解释,转疑为喜,于是登御舆,命舆夫舁之行,将过摄影器时,勋龄已拍一影,慈禧过摄影器后,问是否已摄取其影,得知已摄,很不高兴,曰:“曷不先告余?!……后再摄时,须先语余,俾令面容和悦也。”这天临朝,她竟不管事之缓急,只匆匆坐谕了二十分钟,便宣布退朝,各大臣既去,她即步入朝堂之院内,命舁御座入院,后置屏,下置足凳……又命宫眷取长袍数袭,俾其选择,然后便大拍特拍起来。拍讫,她便要勋龄展示照片,勋龄解释还需在暗室中冲印,她竟说:“此无妨,余愿一往视之,固不问室之如何也!”于是,将近七十岁的慈禧又兴致勃勃地与勋龄、德龄同入暗室,在红光中观看冲印过程,刚冲出负片,她马上取到手中观看,又惊疑为何相上脸、手皆黑?待给她解释还需再印正片的道理后,她感叹说:“原来如此,诚可谓到老学不尽矣!此事以余视之,洵属新颖。今余摄影,中心甚慰!”时已中午,她去休息,下午三点半钟,午睡甫醒,她便匆匆著衣,迥异恒时,衣毕,即赴勋龄处,亲观晒印,当时是用天然日光晒印,慈禧竟不辞辛苦,坐视勋龄操作,足有两个小时之久,既得第一张,手持弗释,更阅其他数张,及复视手中者,讵已变黑,于是再次惊呼:“胡为变黑?!抑晦气乎?!”这时,勋龄的前程,在几秒钟里,恐怕真是悬于发丝了!德龄一旁忙予解释,这时的解释一定要:一、言简意赅;二、使用慈禧易懂的语汇;三、又不能有丝毫令慈禧尴尬的副作用;四、营造出欢愉的气氛。果然,德龄在以上四个前提下,把显影后如不及时用药水定影,相片还是不算最后完成的道理,让慈禧终于明白,于是这位最难伺候的老佛爷方转怒为喜曰:“是诚有趣。”从此她拍照兴趣大发,竟很有点“不爱江山爱照相”的味道。
拍腻了“标准照”,慈禧又大拍“生活照”,并简直允许勋龄用抓拍法随时随地拍摄起来,这都还不过瘾,于是又搞了大量的“化妆摄影”,其中最多的是在颐和园与宫禁内中海荷花丛中所拍的观音照,慈禧自扮观音,她的爱侍李莲英扮韦陀或善财童子,庆王的女儿四格格扮龙女,等等,现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内务府档案中,保留了不少有关慈禧照相的口谕笔录,如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七月,为准备十六日(阴历)的拍照,提前多日便有如下口谕:“海里照相,乘平船,不要篷。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绷。莲英扮韦陀,想着带韦陀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带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要桨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竿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日要齐。”(见《紫禁城》杂志一九八〇年总第四期所引)所以万不要以为在那“多事之秋”里,这位中国独裁者脑子里所装的,皆为军国大策,或只是醉心于与“维新派”的政敌进行“路线斗争”,她实在是用了很不老少的时间开动脑筋,花样翻新,色色精细、奇想迭出地大照其像,也就是痛享了一番这由西方“蛮夷”那边传来的“奇技淫巧”,以至她人虽早化腐灰,而“圣容”却遗留得未免有点“供大于求”了。
从德龄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对西方,实在是很有好奇心的,在维持其自尊心的前提下,她是很愿与西方事物接触,更愿听取种种形容介绍的,她对西方文化,并没有一个决然要抵御的前提。那时的慈禧,已多少具备了一些关于西方的地理、历史知识,不再以为法国、西班牙等无非都是英吉利的狡狯“化名”,以便多向中国索要赔额;她并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甚表钦佩,有时还以彼自比。当她宣谕要甫归国的裕庚夫人带领德龄、容龄两姊妹到颐和园觐见她时,裕庚夫人未免惶恐,因为她们母女都来不及制作满族服装,慈禧却让她们马上穿着西洋裙装入见,她们遵旨去了,慈禧对她们的洋装虽觉奇诡,却又甚感美丽,竟因此命令她们就那么洋装打扮地随侍身边,有一回,听德龄说到西洋人开舞会的事,她竟让德龄、容龄两姐妹在西洋留声机放送的西洋舞曲中,向她演示西洋人的舞姿(该姐妹在法京巴黎曾向后来名声大噪的依莎贝拉?邓肯学过舞蹈,还公开表演过芭蕾舞,因此在慈禧前的表演不过是小示其技),慈禧虽甚感惊诧,却又兴味盎然;直到几个月后,德龄她们感到西洋装扮实在不能适应中国宫廷的生活方式,并且慈禧也终于感到看腻,这才命她们改换满装。在各地高官纷纷向慈禧敬献各种贵重的寿礼时,慈禧难得有看上眼的,但德龄母女从法国巴黎给慈禧订购的化妆品和洋靶镜,却令慈禧喜不自禁、爱不释手;慈禧很乐于接受西方外交使节夫人的觐见,并很注意给对方留下“文明印象”,比如说,在颐和园中,宫眷们,包括光绪名义上的妻子隆裕皇后,当然更包括德龄、容龄等女官,都是绝对不能坐下来吃饭的,即使不在慈禧视野之内也不能坐,可是在颐和园里招待外国使节夫人时,所有与宴的宫眷都有了座位,并且布置得就仿佛从来如此一样--这并非是“维新派”的建议所导致,而完全是慈禧自己的决定。在《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张慈禧与几位洋使节夫人的合影,照片上甚至有一个才几岁的洋女童,俨然站立在慈禧的宝座一侧,面对这种与西洋人亲和的“圣容”,我们很难想像,就是这个慈禧,曾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企盼并支持端王(载漪)等率领“拳民”,将北京的使馆区夷为平地,并将所有洋人从中国大地上予以肉体消灭或扫地出门,毕“攘外”之功于一役,虽然她的“迷乱”只有不长的时间,并付出了扮作农妇,仓促挟光绪出逃西安的惨重而丢脸的代价,可是到勋龄给她大照其相的这一年,她似乎终于悟出,对于西洋人,不管怎么说,你到头来已无法回避,不让他们进来,或把已进来的统统轰走,都已全然没有可能,你只能与他们耐心地打交道。在一九〇三年所拍的与泰西妇人的合影中,我们可以从慈禧的脸上读到这种既无奈又理智的表情。
德龄回忆录称,在美国画家卡尔终于画完了慈禧的油画像后,慈禧问她,卡尔女士可曾问及庚子年的“拳乱”?并由此向德龄痛吐心曲,承认听信端王、澜公(载澜),放纵他们让“拳民”去攻使馆、杀洋人,是铸成了一生中的大错,后悔不迭。德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有人指为不可尽信。其实,从《景善日记》等其他史料可知,慈禧在庚子年之所以终于决心与洋人势不两立、决一死战,是因为听说洋人下了正式照会,要她把权力交给光绪,也就是要她下台,这是她万万不能的。即使有人说洋人的这一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公然外交干预,是端王他们放出的谣言,但来自洋人的这种干预性压力,客观上至少是以不那么正式的方式表达过的,并非子虚乌有,所以,这就启示了我们,到头来,慈禧的所有政治决策,并非一定是她刻意保守,而是她遇事必权衡其对她无上权力是否构成了威胁,在一九〇一年八月自西安回銮北京以后,通过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屈辱苛刻的条约,她感到洋人们似乎并不怎么干预她的权力行使,她的“灭洋”情结反得化解,于是,自那以后,屡有颇具革新意义的诏令经她首肯颁布,如一九〇一年八月銮驾刚歇便命各省于省城及所属府州县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又命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十二月,许宗室子弟出洋留学,命满汉通婚,劝谕女子勿缠足;一九〇二年七月,颁行学堂章程,大体采用日本制度;十二月,派员参加美国圣路易城博览会;一九〇三年二月,命保护出洋回国华商,又派员赴日本考察金本位制;七月,设商部;九月,命各地方大小文武官员振兴商业,公布商会、铁路简要章程;十一月,派京师大学堂学生三十一人赴日、十六人赴西洋各国留学,该月十七日,北京译学馆开学;十二月,颁《钦定大清商法》……而至一九〇五年七月,爽性宣布结束科举,“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十一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时的慈禧,是只要你不去撼动她的权力,一切都好商量。她的权力概念,是以她个人为中心的,比如我们说“《辛丑条约》是丧权辱国”,我们这话语里的“权”,是抽象的“国权”,可是慈禧却只看重是否还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最后还是由她“定盘子”,那就哪怕定的是个向列强割地赔款的“盘子”,或定的是个简直与“革命党”要求并无二异的结束科举的“盘子”,她都觉得并未“丧权”,反之,哪怕你行起权来比她更守旧,或对“革命党”弹压得更严厉,或竟真将“外夷”攘于疆外了,她竟不能“定盘子”,那她也是不能甘心的,在她来说,那才是“丧权”,是暗无天日,是绝不能容忍、接受的。更明快地说,要卖国也得由她卖,要维新也得由她行,要杀洋人也得由她杀,要优待洋人也得由她待,慈禧专制中国半个世纪,她的心眼儿里,装的就是这样的权力观念,她对亲儿子同治皇帝都不放权,同治死后把妹妹的儿子光绪抱来充当傀儡,光绪死了,她眼看也活不成了,到生命结束的前一分钟,她仍想着不能“大权旁落”,一定要再抱一个亲妹妹的孙子(虽为侧室所生)当傀儡,并要她的亲侄女儿隆裕皇后替她再搞“垂帘听政”那一套……
且说慈禧在一九〇一年后虽首肯颁布了一系列似乎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命令,可是她的这一切“开明态度”都来之晚矣,革命党不能饶过她,只承认光绪权威的“保皇党”也不原谅她,帝国主义列强也只是利用她的昏庸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她那里榨取中国油水,既然她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一个工具,派几个洋太太在她面前承欢,送她一些洋玩意儿解闷,让美国女画家给她画像……直到接受她那大幅的“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容”,又何乐而不为呢?
翻看着《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里慈禧太后那一幅幅相片,我把相片里的她仔细端详,忽然有一种麻脊刺心的惊悚。我意识到,在那些相片里,埋藏着一种超越历史评价、道德裁决的更悠远深邃的东西,一种人性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命运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却又能让我们刻骨意会的东西……
是的,那是真的--人,实在是一定时空所捕获的人质。不仅是慈禧,任何一张旧照片里的人物,彼时彼处彼人所凝视的那一瞬,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都能让我们思绪悠悠升腾……


 | 书画频道
| 书画频道